- A+
摄影从西方传入东亚,成为一种新的技术观看和图像存储方式,成为以照片为主要形式的知识生产和文化传播的新手段。在深入观察东亚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有其应有的作用,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的视觉资料。
作为谢子龙摄影博物馆“错综复杂的景象:东亚早期摄影(1850年代-1919年)”研究展的一部分,同名藏品近日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藏品包括多位学者的文章,并呈现给读者560件,其余物品包括照片、浮世绘、明信片、油画和其他各种视觉风格的视觉艺术材料。本文摘自该书。展览策展人顾铮讲述展览中的“东亚及其摄影再现”。这些发生在1850年代至1919年间的摄影实践作品展现了东西方世界的多重摄影视角和重叠视角。东亚社会文化景观。
《错综复杂的景象:东亚早期摄影(1850年代-1919年)》展览现场
摄影与东亚历史
从某种意义上说,长沙谢子龙影像艺术馆的“错综复杂的景象:东亚早期摄影(1850s-1919)”展览是我长期以来的学术兴趣的延伸和深化。早在20世纪90年代,我就曾为当时的《光与影》杂志写过一篇介绍英国摄影师约翰·汤姆森的文章。当时我在国外的时候,对外国人如何代表中国人比较敏感,从那时起我就对这个现象保持着持续的兴趣和关注。 2021年,浙江电影制片厂邀请我策划一个名为“凝视中国——外国人眼中的中国:1850年代至今”的展览。这个展览后来还巡回到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等地。
有时候,一个展览的实现是一个从长期酝酿到逐渐形成一个想法的过程,其中包括我自己的一个野心——积极意义上的野心,通过某种机会逐渐得到证实。这包括我想做的事情。 ,我能做什么,在限制范围内我能做什么?促成本次展览的一个重要契机是谢子龙影像艺术馆收藏了较为丰富的菲利斯·贝托早期的东亚照片。他拍摄的照片启发我思考组织一个更大的展览来展示早期东亚摄影的各个方面的可能性。由此,我展开了一系列的调查,并得到了国内外许多机构和个人的支持。本次展览现为期一年。这只是一个激励他人的展览。希望能给大家一些关于东亚早期摄影的想法。
《鸦片战争图》,铜版画,1843年,爱德华·邓肯,东洋文库收藏
《东京日本桥风景》,木刻版画,歌川芳虎,1870 年,尤里贤三
当然,这也包括个人对展览策划所呈现的“东亚”概念的思考。这里可能有必要概述一下展览的结构。展览分为序言“西势东传:东亚巨变的景象与形象”、第一部分“凝视他者:西方的摄影观察”、第二部分“交错的视线:自我” ——东亚内部考察互鉴》,以及《国外摄影》、《港口风光》、《相关文献》等专题版块。除照片外,展览还包括浮世绘、明信片、年画、版画、油画、画报等视觉风格,展品超过560件。通过这样一个跨视觉媒体的展览结构,我希望尝试展示起源于西方的摄影术在摄影术发明后如何进入东亚,以及如何通过来自“西方”(中国)的西方摄影师首先在东亚展开。面向“东方”(日本和朝鲜半岛),进而引发“东亚”(日本)的东亚内部包容。面向“西方”(中国)的跨国摄影观看的具体实践,展现了东亚东亚社会文化景观东西方多重摄影观看实践中的东亚摄影观看实践中的文化景观,如“软”的展开(如中国早期现代化实践在妇女教育和艺术教育方面的视觉场景)上海)和“硬”(如京张铁路的建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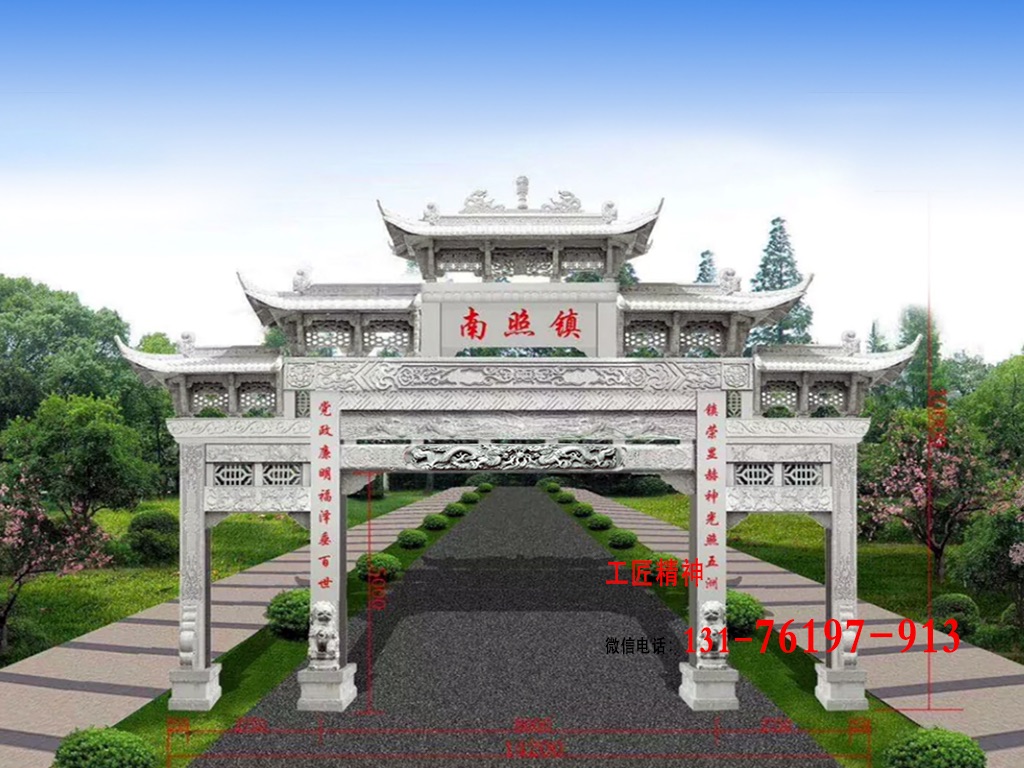
《青龙桥站西上下车同时运行,南看风景》,谭镜堂,1905-1909年,云芝美术馆藏
不同版本的亚洲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展览标题副标题中的东亚概念。这包括东亚,包括中国、日本和朝鲜半岛。它是一个地理概念,但它也是一种想象,尤其是作为视觉想象的对象。到了19世纪,包括摄影术的发明所带来的各种可能性,东亚、亚洲的想象变得越来越可能,窥探的欲望也越来越强烈。 1839年摄影术发明后,作为摄影想象最早对象的东亚开始被人们所观察。本次展览,我们以约翰·汤姆森在1850年代拍摄的亚洲和中国摄影作品为起点,聚焦丁伟和西德。在戴维·甘布尔(David ,1890-1968)等人看来,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终点。
“档案”,艺术微喷,约翰·汤姆森,1868-1872 年,照片库收藏
正是在这个时期,日本思想家、美术史家冈仓天心在其著作《东方的理想》(1903年)中提出了一个很有影响力的理想主义言论,那就是“亚洲统一”“亚洲一体”。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说法是基于明治时期大思想家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非常势利地代表了当时日本的一个主流思潮,即日本不应该与“落后”的亚洲交往,特别是不应该在文化上和精神上接近日本。在与中国朋友接触时,他认为中国是“恶友”。日本是通过帝国主义“黑船入侵”打开国门的。日本在睁眼世界之后,感受到了自己与当时先进、现代化的西方的巨大差距。福泽认为,日本要想崛起,中国不是一个值得结交的朋友,因此必须“脱亚入欧”。但冈仓的“亚洲统一论”认为,“东亚”和亚洲作为文化“一体”,可以为现代人类做出贡献。这种“亚洲统一论”虽然具有与发达西方竞争的亚洲主体意识,但本质上是一种以打败中国和沙俄的日本为亚洲领导者的亚洲主体意识。
《普拉特中日相册》,吉·普拉特,1877-1884 年,盖蒂研究所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展览所涵盖的时代,包括摄影术发明之后,人们对亚洲的想象和理解以及由此产生的再现实践,实际上可以结合这些思想史因素来考虑。冈仓天心的“亚洲统一论”是理想主义的,但也有帝国主义的野心。 1924年孙中山先生在神户发表的“大亚洲主义”演讲,是一种新的反帝亚洲观。东亚思想家的这些关于亚洲的思想实际上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包括今天很流行的、很多人喜欢说的“亚洲作为一种方法”。这些都是对亚洲地理、历史文化与世界关系的思考。
《拿烟斗的少妇》,手绘蛋白版画,费利斯·贝托,1867-1868年,20.4厘米×25.8厘米,谢子龙影像美术馆收藏
对于“亚洲作为手段”这一热门话题,我认为,无论以亚洲为手段、手段的目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如何避免简单化亚洲的手段。我一直觉得没有一个亚洲。亚洲有着复杂多样的文化和宗教背景,它并不是简单到可以概括为反思的对象和内容。具体而言,东亚,即亚洲的一个特定地区,在西方帝国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观中首先被称为“远东”。 “远东”的概念一直持续到冷战结束。渐渐地,西欧、美洲国家开始反思“远东”概念,因为它是从欧洲中心看亚洲和东亚而衍生出来的地理空间概念。现在“远东”这个概念已经消失了,没有人敢再谈论“远东”这个概念了。因为谈论这个概念意味着你提出并暴露了一个关于你从哪里看待它的问题。 “远东”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产物。在西方中心主义受到质疑且极不受欢迎的时候,“远东”叙事已经结束。

《香港,怀抱孩子的中国女人》,蛋白版画,赖芳,1880年代,24厘米×19厘米,谢子龙影像美术馆藏
东亚的形象化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殖民扩张密不可分。东亚,尤其是19世纪摄影术发明之后,被赋予了强烈的一种想象力,同时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观赏的对象。与其说它是一个想象的对象,不如说它是一个被看到的对象。在观看的过程中,有许多复杂的欲望交织在一起。其中有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和地理扩张野心,也有西方传教士认为需要普及宗教价值观以获得新信徒热情的需要。同时,还有人类新知识的产生和对所谓“其他”需求的理解。结合包括摄影在内的各种形式的有关东亚的文字资料,当摄影出现时,或许人们才真切地感到自己掌握了当时有关东亚最科学的经验资料。当然,情况也不完全如此。但必须承认摄影的影响是巨大的。此外,摄影之外产生和感知知识的新方式也受到实证主义观看摄影方式的强烈影响。包括人类的知识形式,摄影术发明之后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我们知道,“看”照片并不是一件简单就能立即学会的事情。我们现在对照片的理解是理所当然的、没有任何障碍的,但是当摄影刚出现的时候,当摄影到达比较早的时候,在某些所谓的野蛮落后的文明与野蛮对比的地区,当你给那里的人拍照的时候,人们在观看时,有时会无法习惯或理解照片等西方图像所呈现的关于自己的形象和知识。
《福建省顾问局会议场景》,三维照片,长城石雕,1909-1911年,9厘米×18厘米,徐西景收藏
摄影师作为一个新职业
摄影术的发明创造了摄影师这一新职业。摄影师在摄影的产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摄影是人类知识的一种新形式:照片。摄影师是影像新技术和知识的大师和传播者,也是人类新知识的传播者。
《远远望布达拉宫》,蛋白版画,青木文教,1912-1916年,10.5厘米×14.8厘米,广东美术馆藏
他们既是图像制作者,又是活跃的行动者,其中许多人利用摄影进行跨境交流。他们将不可见的视线具体化为照片,并将视线矢量化为物体。他们投出目光,然后接收返回给他们的目光,并将其内化为某种东西。沿着他们的跨国行动路线,他们同时编织了一个新的人际关系视野网络。作为不同于画家的新视觉图像的生产者,摄影师是新人际关系和新沟通方式的实践者。
《北京附近的清真寺》,蛋白版画,费利斯·贝托,1860年,29厘米×23.2厘米,谢子龙影像美术馆收藏

观看的多样性与主体性的“觉醒”
通过摄影“看”的行为引起了人们对现实世界的感知的一系列巨大变化。摄影观看不仅是一种新的知识生产方式,也带来了新的认知可能性。从全球帝国主义时代来看,来自西方的目光伴随着征服和殖民野心,也伴随着传教热情、对新知识的渴望等各种欲望。从展览中被“皇帝之眼”对待的东亚照片作为“他者”来看,我们可以发现,来自西方的视角具有一定的控制力,因此也具有一定的压迫性,具有威慑性。的视线。 。通过展览中的照片,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来自西方的摄影作品的压迫性是如何体现的,或者说是如何体现出对西方“他者”的某种程度的尊重。对注视对象()的控制。
《北塘堡》,蛋白版画,费利斯·贝托,1860年,22cm×87.7cm,谢子龙影像美术馆收藏
但观看从来都不是单向的。 “看”不仅是一种压迫、强制行为,更是一种唤醒。这并不是对首先来自帝国主义的观看的辩护。让我尝试对此进行扩展。当我这个“他者”(也是主体)意识到自己被看到时,我的主体性就会在一定程度上被触动和唤醒,我就会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主体性被唤醒的方式并不一定意味着它被重新捕获,包括我这个“他者”如何学习和获得回顾的技能以及如何学习将我作为一个对象(客体)看待的技能和方法,甚至包括寻找我的技能和方法背后的基本思想和世界观的机会。被看见有时也是产生主观性的方式和可能性之一。只是这种观看可能会涉及到一段时间内的屈辱情绪。然而,当我学习并掌握了观看的技巧和方法时,我用它来观看我们自己。这种看到自己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自我意识,首先是从外部看到自己。产生的主观性。这也是对被视为“他者”的反馈。有时,主体性需要通过某种方式来唤醒。主观性自然存在牌坊矢量图,但它是存在于一系列不同的机械关系(包括观看的机制)中的主观性。它需要一定的机会受到刺激,主体才能主动地让自己成为一名摄影师。产生主观性的代理人和演员。
《绳桥上的人》,艺术微喷,西德尼·大卫·甘布尔,1917 年,杜克大学鲁宾斯坦图书馆
在这次展览中,我并没有将摄影局限于从西方观察东亚的一维视角。我不否认观看的这一部分很重要。这些西方的中国形象是从有利的角度观看的(例如,鸟居龙三的中国西南考察之旅受到中国官员的保护),并以文字和照片的形式具有持久的形状,包括西方观众的形象。中国想象力。但这种塑造影响的不仅仅是西方观众对东亚的想象。因为这些东西在西方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国家可能还在流通。这里还有一个更有趣的问题吗?如果大英帝国的汤姆森拍摄了中国,他的中国影像在大英帝国的殖民地仍有一定程度的流传、传播和影响,那么他的影像是否有可能唤醒殖民地人民的自我认识? ? ,代表自己的愿望和能力?有时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和材料来进一步分析,但我们需要认真思考。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些西方摄影家的“看”在多大程度上对我们在展览“交错的视野:东亚的自省与互视”中所掌握的内容做出了哪些贡献和促进呢?技巧和方法甚至是中国摄影师开始记录自己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努力、记录自己实践的一个基本概念?展览的第二部分是关于中国人如何看待自己的,包括京张铁路的照片、丁菊拍摄的中国现代妇女教育和艺术教育的照片、以及作者不详的上海五四运动照片。 。也许这是我最想让大家关注的部分,以达到通过展览引发大家思考主观性从何而来的目的。
《言末女校学生肖像》,丁菊,1920年代,丁菊家人收藏
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最初对摄影的观看具有侵略性、剥削性和视觉掠夺性,但客观上,在一定条件下,它也具有催化和对话作用。
东亚从被动客体到主动主体的转变是我希望在这次展览中触及的话题。这些摄影实践是早期东亚摄影的一种不平衡机制下(来自东亚)再平衡和抗衡的结果。因此,用视觉的概念来组织这次“东亚早期摄影”展览也许更为恰当和合理。当然这有其局限性。

《上海外滩全景画册》(局部),工泰照相馆,1884-1890年,19.5厘米×333厘米,同病学
以摄影方式观察“简化”世界的局限性
有什么限制?摄影媒介的本质至少存在一个固有的限制。
我认为这是因为摄影简化了“世界”。这种简化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本次展览。这是一个必须警惕的限制。首先,摄影本身就是对世界的简化。摄影师拍了这张照片,丢弃了那张照片,将周围与我们身体一样大或更大的现实变成了小照片。这是通过细节压缩来简化。 ,将世界缩小为一张照片。有时我常说,不要害怕照片。无论多么丑陋的事物和场景,它们都会被记录在照片中并缩小尺寸。他们没有什么难看的地方。
《英法联军委员会办公室的外国水手》,三维蛋白版画,皮埃尔-约瑟夫·罗西尔,1859年,8.5厘米×17.5厘米牌坊矢量图,谢子龙影像美术馆收藏
有很多“丑”的东西在照片中是完全看不见的。照片是这个世界的主观和简化的结果。虽然我们说现在有能力释放大量隐藏的细节,但总的来说,凭借机位、取景等技术和概念,在摄影中,一个老手完全可以给出自己对世界的主观解读。个人对世界的诠释。如果一个展览有几百张、几千张、甚至几万张照片,它能给出对世界完全可靠的认识吗?我们必须画上问号,保持警惕。这些照片,包括这些摄影师所做的画框选择,在技术上都是客观的,而且是个人主观的。我们看到展览中有一些相册,涉及到各种因素(包括文字)。比如《横滨写真》写真集,是否能卖得好,就有商业上的考虑。一名摄影师拍摄的数千张照片被制作成包含数十张照片的相册,并变成商品出售。让我们想想世界变得多么简单。
因此,简化的过程是一个“政治”的过程。这个“政治”是指各种因素和力量经过竞争、考量、协商后的再平衡。
作为策展人,我必须根据这些图像材料进行选择。我必须承认,我的选择是主观的,包括我在选择这些照片时所意识到的,我意识到不能在这个展厅展出的,以及我有什么样的惶恐。因此,最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展览,虽然有着前所未有的500多幅作品的规模,但却是通过不断的简约和客观的个人主观性的介入而形成的。对于这样的展览,我们难道不应该警惕和反思吗?
《从栈桥向东的威廉皇帝街摄影》,照片,匿名,年份不详,云芝美术馆藏

以区域为手段的突破
我敢说这次展览是开创性的。为什么?据我所知,世界上还没有以东亚这样的地域概念对早期摄影进行全面的呈现。这有其自身的风险,但今天已经完成了。当我想象这个展览的时候,我会想人们会问什么问题,然后我会做什么。但我实现到什么程度,也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有些想法还是没有实现。因此,这样的展览只能作为现有研究的开拓,为未来带来更大的可能性。未来,我希望有人能举办一个更有趣的东亚摄影展览。
《五四运动中学生游行》,匿名,1919年,丁炬捐赠,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无独有偶,2022年12月至2023年8月,新加坡国家美术馆举办了一场名为“活生生的照片——东南亚摄影”的展览,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我的想法。也就是说,在亚洲的一些地区,有一些人和我一样,也许更多的是用摄影作为一种方式来进行地域性的思考和展览。他们认识到摄影史的研究也可以通过展览的方式来进行,并想到采用地域性的方式,基于认识到摄影等某些视觉媒介具有较高的观看相关性和观赏性的前提。观看内容一定程度的同质化,努力尝试一些不局限于某一国家的摄影做法。某种具有更广阔视角的实验和探索,但始终意识到其中的联系。而这样的尝试和探索或许有助于更好地启发一些问题,比如东亚等地区文化之间的某些历史联系在脱离现代民族国家特定边界的束缚后是否还会继续存在。变得更加明显。在东亚,中国文化通过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当然,我们不能说中国文化是日本文化的母体,但它们在精神上、文化上有一定的联系。因此,它突破和超越了地理位置的界限。通过早期摄影来审视社会生活场景或者在审视摄影本身的过程中反映出来的某些地域差异和特征、媒介特征和局限性,应该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
《吴又如画宝》,石版画,吴又如,年代不详,56cm×26cm(双面),谢子龙影像美术馆藏
或许可以说,无论是从《错综复杂的景象:东亚早期摄影(1850s-1919)》展览,还是从《活生生的照片——东南亚摄影》展览中,我们是否可以看到,在研究中从摄影的历史实践来看,一些通过展览发展起来的研究方法,不一定是一个新的阶段,而是一个新的可能性出现的阶段?也就是说,我们是否有能力以超越现代民族国家边界的方式思考摄影的历史和实践?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是什么?前提可能是文化、传统、历史的延续与断裂,以及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等外部冲击。有了这些前提,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这样的前提下进行的摄影历史研究或许就有了新的可能性和新的现实意义。
书的封面
内页
注:展览“错综复杂的景象:东亚早期摄影(1850年代-1919年)”展览时间为2023年9月16日至2024年9月1日;顾政,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 我的微信
- 这是我的微信扫一扫
-

- 我的微信公众号
- 我的微信公众号扫一扫
-





